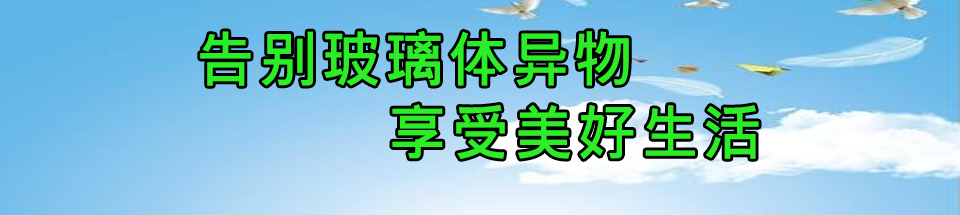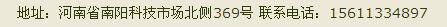活着的二舅
老家山东。因常年在外工作,闲少路长,回家多在春节前后。
年大年初一,去二舅家走亲戚,见到了二舅。心下一酸,60多岁年纪,已经憔悴的不成样子,佝偻着腰,穿着七八层单衣,眼睛浑浊,近视几千度。迈不开腿,一点点往前挪。
我责怪他,去年给他的棉衣怎么不穿,他说穿着热,就压在柜底。回去后,跟我妈说起这事,我妈说,你二舅就这样,是个吃苦人。
二舅,大名李善毕。
年轻时候曾是李堂村生产队的队长。二舅的腿病,据我妈说,是年轻时候给队里浇地,让凉水给激的。
我妈说,老姥爷书读得好武练得好,参加过小刀会,去河北天津一带打过洋鬼子。姥爷去世那会儿,家里还有几架的古书,“一大掐子”铜管狼毫毛笔。也算耕读传家。及到解放后,家里后代学历最高的是我妈这个初中生。我姨和二舅,都是文盲。
年,姥爷姥娘去世的时候,我妈才十来岁,二舅也还不到二十。大舅参军后,二舅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扛着日子往前过,张罗两个妹妹体面出嫁。两个妹妹不忍心自己二哥打光棍,找人"买"了一个媳妇。
上个世纪80年代,村里人对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无从感知,父辈们只记得村里刚刚通电,地刚刚包产到户,鲁西北一带,被人贩子从云贵川拐卖过来的妇女很多。听我父亲说,二妗子是彝族,四川人。三十年后的我再回忆起二妗子,之剩下留下的齐耳短发以及怪异的口音。
我记得小时候每次去李堂村,基本是去参加某个亲戚的葬礼或者周年祭。大妗子去世,三十多岁,留下三个孩子。我妈带我去吊唁。
鲁西北妇女哭灵如歌,抑扬凄苦,放声之时,口有哀号。二妗子乡俗难入,哀从心来,只把脸埋在臂弯里呜呜的哭。周边围了一圈野性难驯的孩子,嘲笑二妗子的哭法。有大胆的还去揪二妗子的辫子,后被我妈怒骂驱散。
年,二妗子进家之后,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表姐焕霞。我想,那几年应该是二舅最幸福的时光。
我妈说,焕霞姐小时候聪明伶俐,见人就笑着打招呼,左邻右舍都喜欢。但自我记事时,焕霞姐就已经傻了。
村里人说,她三四岁时候跟着别人去邻村看电影,回来走散了,大深夜一个人走回家,许是碰见了什么,就迷傻了。我妈说,可能是深夜惊吓,再加上高烧,没及时看,“脑子烧坏了”。我妈和我姨心疼,带着去县里看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好。
焕霞姐就这样傻了。
见人还会笑,但已经让人一眼看出傻气。大小便可以自理,但不避人,穿衣服慢慢教也会了,叫吃饭就吃饭,时不时嘿嘿自个笑。村里人都喊她,傻焕霞。
二妗子自始至终都未能融入到鲁西北的乡俗里。口音难改,村里人听不懂,脑子也不太清楚。里里外外,多是二舅一个人操持。许是之后也见过几次,但印象都湮灭了。我只记得最后一次见二妗子,是在一个夏天的夜里。随父亲去二舅家送药。当时二舅不在,只有二妗子在家。父亲就着昏黄的油灯,一字一顿地给二妗子说药的用法,二妗子一字一顿的重复着,点着头。
这或许是永别。
长年在外读书,等我有次回家,我妈和我说,二妗子去世了,乳腺癌。二妗子没有来处,也没有娘家可以报丧,停灵一天后埋葬入祖坟。
死了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要活着。
于是,二舅和焕霞姐相依为命。按时节种地,农闲养羊养牛,贴补家用。怕人偷,把牛羊养在堂屋里。气味熏人,卻人十步以外。
我妈抽出空来,就做些馒头包子等,带着去二舅家里看看,给他们洗洗补补。我也慢慢长大,求学在外,见二舅和焕霞姐的时候也越来越少。
我们家是寻常农户,靠天吃饭,供着三个学生上学,日子紧巴。二舅养羊养牛卖了钱就送到我们家。说是自己不识字,让我爸妈帮他存着。其实我家知道,是让我们先花用。
二舅是真不识字,过年的对联能贴反了。不是上下联反,是字能贴颠倒了。大年初一去的时候我每每会替他纠正过来。二舅虽不识字,但口才和世故却是清透。平时在四里八乡说媒,也能赚些烟酒钱。
在我高二时,大我一岁的焕霞姐结婚了。
男方是一个三十多的光棍,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有一个瞎眼老娘。
鲁西北风俗,初二是新女婿上门的第一天。二舅特意做了两桌子菜来招待。
按照习俗,有些村妇要给新女婿抹灰,那个粗汉,慌里慌张,话都不说一句,撂下筷子,骑上车就跑了。留下一阵哄笑在身后。
从二舅家回来,我还问,焕霞姐这么个情况,还结啥婚?我妈说,你二舅越来越老,照顾不了她一辈子,再傻,有人要,结了婚就算有了个家。当时,没有社会阅历的我无法反驳。
再后来,听我妈说,那个男人把焕霞姐打住院了。好了之后,二舅就把焕霞姐接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那个男人由本村长者带着上门赔罪,被二舅训斥了一通后,又把焕霞姐接了回去。
等到我大一时,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焕霞姐死了。或许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来。
后来,细节一点点填补,才知道了焕霞的死因。
焕霞姐不能自理,那男的又蠢笨,不会照料,焕霞饮食不洁,拉肚子,也没管,就一直拉肚子,直到脱水而死。
知晓后,我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来。从文的我,钻研过小说和电影编剧,自信对人的各种结局有很强的接受能力,但当知道焕霞姐的死法之后,控制不住的悲从心来,欲哭无泪。
少年丧亲,壮年丧妻,中年丧女,我无从安慰二舅,也无法探知二舅内心深处,是如何开解这无穷的哀痛。只是在节日时的饭桌前,在烟酒引起的剧烈咳嗽止息后,看见过几次他擦拭眼角的泪滴。眼神混浊,像看着什么,又好像没看着什么。
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依然要活着。
于是,二舅和牛羊相依为命。怕人偷,还是把牛羊养在堂屋里。气味熏人,却人十步以外。
有次回家,正遇见二舅来我家,一问,腿疼到无法骑车,就走了一上午到我家,让我妈带他去看看眼病。说,眼前老是灰蒙蒙的,老感觉这天儿像黄昏。医院看了眼病,医生说,眼睛玻璃体混浊,到他这个年纪,“已经看不好了”,又看了腿,买了吃的贴的一大堆药。送他回家,在昏黄的点灯下,我一字一句的嘱咐他药的用法,他一字一句的重复着,点着头。然后,我想起了二妗子。
年大年初一,我坐在二舅家清冷的堂屋里,背对着身后的牛羊,面对着二舅张罗的酒菜,听着他因抽烟呛出的咳嗽声,把我母亲给他捎带的吃的喝的拿给他看,一边问他近况一边责备他抽烟喝酒太多,二舅眯缝着眼听着,应付着“也不多也不多”,心虚的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按照老家礼仪,向堂屋八仙桌祖先牌位磕头,然后面向二舅,口里称:“二舅,给您拜年了”,跪下磕完,二舅拉起我“别磕了别磕了”,恍惚间像拉起自己的孩子。
当我拜别,二舅一直站在家门口目送我远去。瘦小的身影在北方寒冬里愈发单薄。
回忆如果还存有美好,前路或许也没那么苦涩。
我一直记得,08年初夏,我辞职后在家休养,妈让我开着农用三轮车去帮二舅收麦子。
阳光明媚,南风怡人。
二舅站在高高的垛顶,叼着根烟,间或咳嗽两声,搬着小麦袋子一一码好。姨家大表哥说,累了歇歇。我妈笑着说,大庆,恁看恁二舅都60多了,还不觉累呢。大庆哥说,可不,别看俺二舅瘦,可有劲着嘞!
二舅直起腰,看了看自己黑瘦的胳膊,半截香烟在嘴角一上一下,挥洒了些许自豪:“可不,我这,还能再干几年呢!”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年代那个生猛的生产队队长。有着大把气力,有着大把心劲儿,活下去,把日子过下去。
▲图片▲:二舅去济南看望大舅时留影
以上,写于年,那时二舅仍活着。
那时我还相信,只要二舅今天比昨天好,之后的日子就还有过头。
但二舅的明天没有比今天更好。
在年,二舅因眼疾愈发严重,又无法动手术,生活渐渐不能自理,后大舅家表哥和我妈、姨商量,经二舅同意,把他送到了县养老中心,一个月块的费用,用我妈的话说,能吃上热乎饭了。我妈和我姨经常坐乡村中巴去给他送些吃穿用的。
后来许是因为离家远,我二舅又去了隔壁镇敬老院。因为近,我妈能每周开车电动三轮把他接到家里,做顿好吃的给他,临走又给他带上吃的喝的。听到这,我也心下有些许安慰。也许,二舅晚景不会太过凄凉。
可没想到,就在当年暮秋一天,敬老院早饭,二舅未起床,敬老院护工也没查看,待到第二天清早,方感觉不对。当时二舅已经昏迷。院方赶紧联系我妈,我妈又叫上我爸、医院。
在ICU一个月,没有意识。医生说,大面积脑溢血,如果发现的早,或者还能苏醒,但现在这情况,救过来也是个植物人。
老家县城的ICU,每天几千块。一个月后,二舅不治。或者是情况恶化,或者是一众在场亲人放弃。我无法还原,也无力再事后追问。后来我妈跟我说,这样也好,不用再受苦了,你二舅,一辈子苦命。
停灵一天,然后火化,二舅进了祖坟,和死去二十多年的二妗子相聚了。
或者他们会再去另外一个村,去看望躺在那个村子地里的焕霞姐,一家三口团圆。我宁愿相信,在天有灵,泉下有知。
听人说,人会经历三次死亡,第一次是断气,生理死亡;第二次是葬礼,社会死亡;当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去世了或者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才算真正地死了。
因此,我想,也许二舅还“活着”,活在亲人们的脑海里,活在我的记忆里。在每一个过年、清明、农历七月十五的时节,在坟前上一刀黄纸,在黄纸燃烧,灰烬飞扬之时,追思也随之飘远。
那一刻,我宁愿相信,二舅在天有灵,泉下有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loqky.com/wadzz/92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