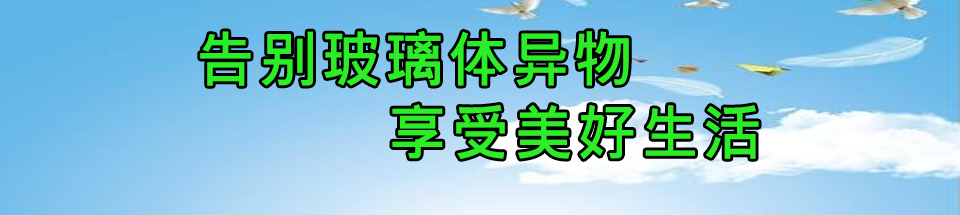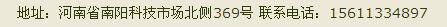城中荐读我的母亲是春天当代名家写母
威海市城里中学
仁★义★博★雅
(一)用什么来报答母爱
■周国平
母亲八十三岁了,依然一头乌发,身板挺直,步伐稳健。人都说看上去也就七十来岁。父亲去世已满十年,自那以后,她时常离开上海的家,到北京居住一些日子。不过,不是住在我这里,而是住在我妹妹那里。住在我这里,她一定会觉得寂寞,因为她只能看见这个儿子整日坐在书本或电脑前,难得有一点别的动静。母亲终归需要有人跟她唠唠家常,而我不能使她满足。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的一生平平淡淡,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她也许是一个有些偏心的母亲,喜欢带我上街,买某一样小食品让我单独享用,叮嘱我不要告诉别的子女。可是,渐渐长大的儿子身上忽然发生了一种变化,不肯和她一同上街了,即使上街也偏要离她一小截距离,不让人看出母子关系。那大约是青春期的心理逆反现象,当时却惹得她十分伤心,多次责备我看不起她。再往后,我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去广西工作,然后考研究生重返北京,远离了上海的家,与母亲见面少了。
最近十年来,因为母亲时常来北京居住,我与她见面又多了。当然,已入耄耋之年的她早就无须围着锅台转了,她的孩子们也都有了一把年纪。望着她皱纹密布的面庞,有时候我会心中一惊,吃惊她的一生过于简单。她结婚前是有职业的,自从有了第一个孩子,便退职回家,把五个孩子拉扯大成了她一生的全部事业。等我自己有了孩子,才明白把五个孩子拉扯大哪里是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很少听见她谈论其中的辛苦,她一定以为这种辛苦是人生的天经地义,不值得称道也不需要抱怨。
作为儿子,我很想做一些令母亲欣慰的事,也算一种报答。她知道我写书,有点小名气,但从未对此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直到不久前,我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当我女儿在她面前活泼地戏耍时,我才看见她笑得格外的欢。自那以后,她的心情一直很好。我知道,她不只是喜欢小生命,也是庆幸她的儿子终于获得了天伦之乐。在她看来,这比写书和出名重要得多。
在事关儿子幸福的问题上,母亲往往比儿子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倘若普天下的儿子们都记住母亲真正的心愿,不是用野心和荣华,而是用爱心和平凡的家庭乐趣报答母爱,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
(二)妈妈在山岗上
■陈建功
四年前,妈妈过世三周年那天,我到八宝山骨灰堂取回了妈妈的骨灰——按照当时的规定,三年期满,骨灰堂不再负保管的责任。远在广州的父亲来信说,还是入土为安吧!
可是,哪里去买这一方土?四年前那时候还不像现在,现在倒新辟了好多处安葬骨灰的墓地。那时,只有一个别无选择的,形同乱葬岗子的普通百姓的墓地。我去那里看过,普通百姓身后的居处和他们生前的住处一样拥挤。我辈本是蓬蒿人,把妈妈安葬在这里,并不委屈。然而,想到性喜清静的妈妈将挤在这喧嚣的、横七竖八的坟场上,又于心何忍?
对官居“司局级”方可升堂入室的“革命公墓”,我是不敢奢望的。假若妈妈是个处长,说不定我也会像无数处长的儿子一样,要求追封个“局级”,以便死者荫及子孙。而我的妈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非分之想或许有过——为妈妈买骨灰盒的时候,不知深浅的我,要买一个最好的。我当即被告知:那必须出示“高干证明”。从那以后,我不敢再僭越。现在,妈妈躺在80元一个的骨灰盒里。最后,我把妈妈的骨灰,埋在我挖过煤的那座大山的山岗上。
那几天,我转悠遍了大半个北京城,终于买到了一个刚好容下骨灰盒的长方形玻璃缸。又找到一家玻璃店,为这自制的“水晶棺”配上了一个盖。一位朋友开车把我送到那座山脚下。
那些曾经一块儿挖过煤的朋友,现在有的已经是矿长了,有的还是工人。不管是当了官的,还是没当官的,谁也没有忘记我的热情好客的妈妈对他们的情分。我们一起动手,把骨灰盒埋下,堆起了一座坟头,又一起把那巨大的汉白玉石碑由山脚下一步一步抬上山来。
石碑俯瞰着那条由北京蜿蜒西来的铁路。我十八岁那年,列车就是顺着这条铁路,把我送到这里当了一名采掘工人的。
妈妈病故的时候,年仅五十五岁。一位作者讲过自己过生日的惯例:那一天他绝不张灯结彩,也绝不大快朵颐。他把生日那天作为“母难日”,因为自己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太大的痛苦。
“母难日”三个字,使我动容。因为我不仅是在出生那天给母亲带来痛苦的儿子,而且是给母亲带来了终生灾难的儿子。因我的出生,使妈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而母亲如此过早地亡故,恰恰是由于心脏病的发作。
我没有更多的话好说。好好活着,充实,自信,宠辱不惊,像妈妈期望的那样。山岗是普通的,妈妈也是普通的。每年清明,我都去看望山岗上的妈妈。
(三)买一张车票去看母亲
■高建群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我什么时间有了空闲了,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陪母亲住一段时间,吃她做的饭,跟她拉家常,捧起一本书读给她听。这文章写了几年了,可是我始终是一个忙人,无暇脱身。
前几天,站在家里的阳台上,怅然地望着北方,我突然明白了,忙碌的人生是永远不会有空闲的。你要去看母亲,你就把手头的所有事撂下,硬着心肠走,于是,我买了一张火车票。
火车轰隆隆地开着,开往山里。这条单行线的终点站就是小城。母亲就在小城居住。我是从四十岁头上,突然开始恋家的。是不是人步入这个年龄段以后,都会突然产生这种想法,我不知道。
母亲是河南扶沟人,十四岁时完婚,十六岁时生下我的姐姐,十八岁时生下我,二十岁时生下我的弟弟。我的父亲于七年前去世,如今这家中,只母亲一个人居住。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母亲了,在母亲的家中,我幸福地生活了一个礼拜。我说我有胆结石,一位江湖医生说,多吃猪蹄,可以稀释胆汁,排泄积石,我这话是随意说的。谁知母亲听了,悄悄地跑到市场,买了五个猪蹄,每天早晨我还睡觉时,母亲就热好一个,我一睁开眼睛,她就将猪蹄端到我跟前。
在回家的一个礼拜中,我收敛起自己的种种人生欲望,坐在家中陪着母亲。小城的朋友们听说我回来了,纷纷请我吃饭,我说饶了我吧,我这次回来只有一件事,就是陪母亲。
“热爱自己的母亲吧,朋友!这是一个失去母亲三十年的人在对你说话!”这段话,是前苏联作家卡里姆说过的。此刻,我也想说,如果你的母亲还健在,不妨抽时间多去看看她,这世界并不因你离开的这段日子而乱了秩序,而你会发现,这段日子你做了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四)母爱致命伤
■池莉
爱是好东西,好东西也伤人。爱尤其容易伤人,伤人最深的,往往又是最爱。
要说母爱,那正是爱之最了。其他种种爱,都不比血浓,只要你铁了心,都可以躲开,可以了断,可以删除,可以遗忘。唯有母爱,是命定,是天生。一个女人,只要经历了十月怀胎,经历了一朝分娩,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从此,没得说,无理由,必定母爱泉涌。
因此,也就,母爱最难把握。母爱突如其来、浓烈深厚,让女人自己都身不由己,也就极易膨胀、霸道与专横了。许多子女,对母亲的最深记忆,多是那些很难讨人喜欢的妈妈式系列训斥:不许哭!别乱跑!听我话!吵死人!赶快睡!多穿点!让你穿就穿!要你吃就吃!听到没?长耳朵没?现在、立刻、马上、必须,去给我上培优班!不许玩手机!不许早恋!必须要有事业心!这个工作你选的不对!这个对象你选的不对!你没经验必须听我的!该结婚了快快快!该给我抱孙子了快快快!该常回家看看了快快快!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你啊!你就这样不孝不敬吗?
可悲就可悲在这里,子女已经很受伤,作为分泌母爱的母亲,却丝毫不以为意,强势母爱任性泛滥:反正一切都是为孩子好!反正将来孩子总会知道的!事实上,将来孩子真不一定知道。再说世事无常,谁敢保证一定会有那么一个将来呢?可怜最好的母爱,也会有这样一种致命伤。
母爱致命伤,还更有凄绝的一种,那就是:母子有分无缘。母爱兀自奔涌不息,却都只积郁在心、淹没自己,子女全然不能够领会。子女堵住爱,母爱会愤怒。母子不亲。都不想看对方。或没话说。或恶语相向。久久不见也想念,刚刚相聚又讨厌。母亲心凉透,自叹命苦。其实孩子也倍受良心折磨。
可见母爱的施与与子女的收受之间,有太多误差和歧路。理想主义的母慈子孝与现实的具体生活,有太多悖论和矛盾。万幸的是,母爱又是伟大的。具有伟大特质的母爱,是拥有一种超常宏伟阔大的宽容能力。有些天生伟大的母亲,甚至还躺在分娩的血泊之中,就已经懂得如何目送自己孩子了。在脐带剪断那一刻,在护士抱过去那一刻,她的孩子,就已经进入了社会,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人。她的以目相送,是大树对另一棵小树的看顾,是豆荚对一粒青豆的赞许,是在漫长岁月中,长江后浪对前浪的默默推送,绝对没有要求前浪必须回报后浪。
伟大母爱,并不在于对子女说一千道一万谆谆教导永不停嘴,而在于明智。明智的母亲,只做一个动作:少说为佳。对于子女,哪怕操碎了心都能够闭得住嘴,少说为佳,这是真伟大。
值得天下子女记取的是:这个世界,几乎没有绝对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接近绝对,那只能是母爱。不管母爱伤你多深,不管你对母亲有多少不满,真的你得明白,她只是爱的方式不对,她只是不够伟大。芸芸众生,凡身肉胎,不够伟大不是缺点。谁不想伟大呢?让母亲慢慢来。而每个孩子,也都是未来父母,对于伟大是需要学习与修炼的,醒悟得越早越好。醒悟并开始运用这份醒悟,幸福就已经敲响你家大门。
(五)我的母亲是春天
■宗璞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养,亲友的联系,这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我会活下来。
在昆明时我严重贫血,站着站着就会晕倒。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晒太阳半小时。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不论多忙,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一分钟不能少。
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母亲费尽精神护理。用小匙喂水,用凉手巾覆在额上,有一次高烧昏迷中,觉得像是在一个狭窄的洞中穿行,挤不过去,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亲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我是平安的。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也是母亲,一医院,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其实是母亲陪我。我过了四十岁,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
小学时曾以“我的家庭”为题写作文,我曾写出这样的警句:“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很重要。”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父亲(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回来向母亲描述,对自己的地位似并不在意,只顾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
在父母那个时代,先生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其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亲特别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发无间。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母亲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没有什么东西吃的情况下,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医生的诊断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qky.com/ways/62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