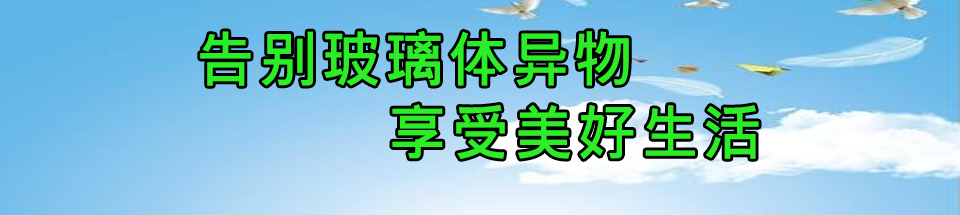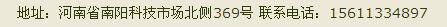温柔地倾诉
本文来自于全国著名眼整形专家徐乃江教授的回忆录。字里行间真实记述了他青年求学、投身眼科、文革遭遇、开创眼整形专业、培养大批年轻医生,从医60余年的深切感受。20世纪90时代,中国眼整形业内有“南徐北赵”(医院眼科赵光喜教授)之说。曾受聘谢立信院士和何伟教授所在单位的客座教授,可见徐乃江教授对中国眼整形事业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祖父是一名中医,在我故乡那个小地方(江苏靖江八圩港)小有名气。家父是上海同德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不久便在清江浦(淮阴,现属淮安市)医院任院长之职。医院,七七卢沟桥事变进入全面抗日战争大片国土沦陷后,江苏也很吃紧,医院奉命内迁,经过武汉、长沙、芷江等地最后定点在湖南湘西小城市乾城(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乾州县)。在那里开始了我六年的小学生涯。由于地处湘西崇山峻岭之中,交通极不发达,既无电灯,也无自来水,夜晚点的是油灯(桐油或茶油,用灯草做灯芯)照明。稍微讲究的一点就是洋油灯了,这是大人们打麻将时才能用的。逢年过节就用油汽灯,很是明亮。偶尔有放映队用自带的发电机放一场无声电影。每月有四次赶集,那时是商品交易最热闹的时候。我们穿的都是当地土布做的衣服,当地人夏天多穿草鞋。我也常常穿着用麻织成的草鞋去上学。
在小学六年中很少在晚上做作业,更没有补习班之类的课外活动了。课余就是打篮球、滚铁圈、花式滑滑梯或者放学后到南门外或北门外的河里去游泳。南门外河大,筑有一座水坝为碾米厂提供动力,河边洗衣妇也较多,她们洗衣都用棒槌敲打衣服。游泳时必须穿衬裤(那时没有游泳衣裤的概念),我们更喜欢到更远北门外的河里去游泳,因为那里没有女人洗衣服,人也少,全是像我们这些顽童在“裸泳”。
小城清静而安详,周围群山环绕,城里的青石板路在雨后闪闪发光,空气极为清新。当地人也很淳朴,一般是一日二餐,都是干饭。在我童年记忆中的美食是牛肉巴巴、醋萝卜及糯米巴巴,辣椒是每餐必备的。
由于地处深山老林,又不是战略要地,在八年抗战期间这里没有受到过日寇飞机的轰炸。但由于乾城是汉、苗、土家族混杂区,常有民族矛盾爆发,时常发生械斗,也有一些伤亡。当地老百姓对我们内迁的人称为“下江佬”,内迁到乾城的最大单位是国立第八中学,是从安徽内迁的。学生不少,家姐、家兄都曾在那里求学,抗战胜利复原后,转到江苏省立昆山中学继续求学。
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封闭的乾城,大家都欢欣鼓舞,特别是我们“下江佬”背井离乡,早就盼望回到故里,就等着国民政府发放遣返费了。我终于在年回到了故乡,于年到上海进入上海市陆行中学就读,直到年高中毕业。
年高中毕业时,正值国家进入建设高潮时期,急需各方面人才,为了扩大招生,国家进行大规模高校院系调整,增添了许多专科。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在报考大学时,第一志愿是上海医学院医疗系,考试时我一点也不紧张,也没有人陪送,因为是扩大招生,几乎没有不录取的。报到时发了一枚上海医学院的校徽,佩戴后有些许激动和自豪,因为上海医学院是医学院中的名校,也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同时录取的同学,有的分配到医专科,其中一个专科是专修眼耳鼻喉科的(原定为两年,后改为三年制),这个班级培养出不少眼科专家,如嵇训传、王文吉、胡诞宁、李子良都出自这个专修班。入学后2个月左右,上海医学院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而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及中法牙专合并而成立的医学院,被命名为上海第二医学院。在更换校徽时,大家都舍不得更换上海医学院的校徽。
我们学校师资力量很强,大多是老协和医学院或上海医学院自己的毕业生留学欧美后回国的,一旦进入上海医学院任教后就不允许自己再开业。
由于我喜欢唱歌,入学后不久便被学生会任命为合唱团副团长。除了合唱团,还有舞蹈团、摄影社、文学社等社团,每周活动一次。我们合唱团先后聘请过上海合唱团、音协合唱团的指挥或演员做声乐老师。那时,我国全方位向苏联学习,所选的合唱曲大多是苏联歌曲,如“遥远的地方”、“海港之夜”,或者一些民歌如“阿拉木汗”,也有一些战斗味很强的歌曲。社团生活为枯燥无味的基础医学环境调剂了气氛。
基础医学中不乏知名教授,解剖学郑思竞教授,组织胚胎学王有琪教授,病理学谷镜妍,药理学张昌绍教授等。外语则学习俄语两年,由留沪白俄鲍格巧夫担任,另配一名俄专(上海外国语学院前身)毕业生为夏老师做助教。
医学基础死记硬背的多。我很不适应,所以学习成绩平平。到了临床基础课时,我对医学兴趣逐渐加浓,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
那时大学实行全体助学金制度,除了学费外,每月还有十元零五角的伙食费,所以在校吃饭也不要钱,看病也全部免费。这个制度实施了3年,以后也只是每月交一定伙食费,但学费还是全免。
学制是5年,临床课要有临床思维能力,特别是在导师查房时,我的这种能力表现得更为突出,我的学习成绩也更上一层楼。在临床教学中,诸多名师至今我难以忘怀,如外科学的黄家驷院长、石美鑫教授,内科学的林兆耆教授、钱悳教授、妇产科王淑贞教授,小儿科陈翠贞教授。而眼科则由郭秉宽教授和何章岑教授授课。眼科课时很少,讲义也只是薄薄的一本。临床实习时眼科也只有二周时间,是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眼耳鼻喉学院,即现在的复旦大医院实习的。带教的是和我一起进上医的五官科专科毕业的助教嵇训传医师(后担任该院院长、青光眼专家)。
那时临床实习采用苏联的方法,即三年级结束后暑假进行第一次临床实习,目的是对临床课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我们20多位同学被分配医院,主要实习普外科,共两个月时间。第五学年进行第二次临床实习,医院(内科学院)实习。到了实习最后几个月,我还被任命代理住院医师,那时还要带低年级同学下乡进行抢收抢种等农活,我们作为保健医师和带教老师,而那时诸仁远教授刚入学,他作为一年级的新生,我还带教过他呢。他的一口浙江诸暨口音,擅长发言给了我深刻印象,也不会想到如今他已是著名的视光学专家,见了我也总是称我为老师兄。
我本应年毕业的,由于病休一年,到了年才毕业。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生分配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共有18位同学,我医院(医院,医院)眼科工作。眼科主任是聂传贤教授,他同时也是分管教学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副校长,没有副主任,有五位主治医生,三位是老震旦毕业的,二位是同济毕业的,我上面还有三位住院医生,二位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位是浙江医科大学眼科四年制的毕业生,以后分配来的住院医生清一色是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留校的。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有这样的看法:上海第一医学院师生正统,工作严谨,生活朴实,而上海第二医学院师生则是海派,比较随和,上下级医生的关系比较融洽。医院后确实感到这里的医生打扮入时,工作气氛轻松。那时做住院医生基本24医院里,到周六才骑自行车回家,宿舍是四人一间,晚上基本是阅读书刊时间。但是眼科专业的书籍及杂志很少。杂志就是西安光华印刷厂翻印的美国眼科杂志(那时中国未参加日内瓦出版同盟,盗版并不违法)及中华眼科杂志等有数的几本刊物。
在头两年住院医生期间,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业务进步很快,已能掌握眼科常见病的诊治工作,也能做些门诊手术如翼状胬肉切除、内翻倒睫矫正等。在住院医生的第三年,我便在上海眼科年会上宣读《32P敷贴治疗角膜新生血管》的论文。那时眼科设备极为简单,就是裂隙灯显微镜和眼底镜。眼压测量是采用Schotz压陷式眼压计;周边视野检测是通过人工旋转用示标移动完成,平面视野检测是用一块黑布,上面标有生理盲点,也是用示标移动完成;视网膜脱离复位用的是英国Keeler电凝器(球内异物吸出也用得上),几年以后才进口冷凝器。医院眼科(我科)的看家仪器是一台法国进口巨型电磁铁,所以球内异物和眼外伤诊治便成为其专科特色;另一特色是鼻腔泪囊吻合术。我们科主任设计了一种皇冠样带齿轮的电钻头,放在牙科钻上在鼻骨上钻孔,加快了手术速度,也减少了敲击骨头造成患者的不适。
年,我刚进眼科适逢大跃进和大炼钢铁,造成眼外伤、球内异物的病人骤增,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振仁,当时也罹患眼巩膜穿孔伤及球内异物,经我科手术取出而愈。两年后全院举行文艺会演,我将此事“添油加醋”编写了一 幕话剧“光明之路”,里面当然有进步和保守两种思想的斗争。刚好有一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在耳鼻喉住院行扁桃腺摘除术(那时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妇产科属同一联合党支部),就请她当导演;布景是请另一皮肤科病人是一工厂的工程师策划炼钢场面;我是男一号,女一号是位皮肤科医生,通过这台戏的演出,促使了这位皮肤科医生和这位工程师的联姻,曾成为一段佳话。
那时白内障多做囊内摘除术。当时尚无冷凝器,都是用一镊子(Arruga镊)抓住晶体赤道部,另一手用斜视钩压迫六点钟角膜缘慢慢娩出白内障。由于囊膜破损几率高,所以要求白内障摘除技术必须成熟才能进行,否则囊膜破损后透明的晶状体皮质不能辨认,到第2天换药时就会看到大量皮质残留。如有玻璃体溢出,为了防止瞳孔上移,就用虹膜剪在六点钟方位作一虹膜切开。青光眼多做虹膜嵌顿术或角巩膜切除术。角膜移植手术也开展,但无Helon等充填剂,只好术前静脉滴注甘露醇,压迫眼球尽量降低眼压,用消毒空气注入前房以保护角膜内皮。当时无10-0尼龙线,就将5-0丝线一劈成三股,用其一股穿过3mm?×6mm?三角针间断缝合。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也挽救了不少患者的视力。在这期间,还经历了所谓3年自然灾害的磨练,那时,因为营养缺乏,我得了营养不良性肝肿大,医院发给我克葡萄糖粉,算是为我增加营养,但也总算挺过来了。
年恢复招考研究生制度,招收年入学的研究生。考前有2周复习功课的假期,就冲着2周的假期我也要报名。次年,我终于被录取。
我的研究课题是《青光眼患者房水蛋白的改变》,因为房水量小,需要用电泳法测量,所以基础课除了外语、马列主义理论外,我还选泽了生物化学。在3年学习尚未完全结束时,十年浩劫(“文革”)开始了,研究生被批判为精神贵族,研究生队伍也就此解散了,除浏览大字报外,更多的时间是阅读业务书(因为在读研究生时,每年都发书籍费,我买了不少中国翻印的外国专业书)。
在“文革”中,我参加了工农兵大学试点班的带教工作,这是我一生中业务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医院眼科医疗力量”为籍口,医院眼科,年5医院,从此开始了我从事眼部整形的事业。
医院口腔科和整形科是从医院(医院)迁过来的,也是医院的特色科室。其他的医技力量都很薄弱,其眼科在上海业界也缺乏知名度和特色,只能应付日常的医教工作。进入医院眼科后即担任了科负责人(还有另一负责人),当时无科主任一职。那时,我就筹划要利用医院的整形特色来发展眼科——即向眼整形方面发展。当时我家住在北京西路上的上海医学会图书馆旁边,该馆内有好几本眼整形方面的原版书籍,我如获至宝借回家,请我们劳保单位上海复印机厂的工程师全书复印,我大概复印了5本,从此开始学习眼整形方面的知识,涉足眼整形专业,有时也到本院整形外科观摩手术。
年10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眼科也积累了不少眼整形方面的临床经验。为了扩大医院眼整形专业的影响,我想应该是写专著的时侯了,于是在年我主编并出版了第一本眼整形专著——《眼成形手术学》(参加编写的还有美籍华人刘顿(DonLiu)医师和医院张晓蕴院长),对推动国内眼整形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也提高了医院眼科眼整形方面在全国的知名度。同时,我每年医院讲授2个晚上的“眼整形”课程,对象是该院的进修医师们,同时还有较多我院的进医院的眼科医生前来听课,每次课后都有不少感兴趣的医师争相提问题,学习气氛活跃。
这也启发我在全国办学习班的想法。第一次学习班是由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新技术新疗法学组和福建省眼科学会主办,由我和医院的赵光喜教授主讲。我们每人还配备了一名助手,协助授课期间的手术示教、电视转播。参加学习的医生有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学习热情很高,多数医生从此将眼部整形做为自己的专业重点。不久,新技术新疗法学组取消。我就和当医院联合举办了多次学习班,如与中华医学会广州医学分会、医院、广西桂林第医院、医院等都办过眼整形学习班。
和李凤鸣教授在重庆合影
20世纪70年代末,医院眼科确立了以眼部整形为特色的科室发展方向,但那时只有硅橡胶材料,不像现在有羟基磷灰石、高密度聚乙烯、钛板、钛网、玻尿酸等人工材料。当时我们用得最多的是自体肋骨、肋软骨、髂骨、真皮和阔筋膜。如眼球摘除后上眶区凹陷就取肋骨填充(第一例是由本院胸外科医生示范切取),以后都由我们自己完成。切取肋骨中,先后有4例发生过气胸,都经过负压吸引治愈。联想到现在有如此之多的人工材料,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
和邱孝芝教授合影
由于医院眼科在整形方面知名度的提高,进修医生回原单位后,如遇较疑难病例往往邀约我前去手术或讲课,所以常在节假日或休假期间前往手术,就是现在的所谓“走穴”,可以这么说我是上海眼科“走穴”的领军人物。当时没有多点执业之说,“走穴”属违规行为。实际上我认为“走穴”有很多好处,一可帮助患者就地解决就医问题;二是可以交流经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三是可以增加科室的知名度;最后当然也增加了个人收入。在上海我也有固定的挂钩医点,晚上常常带下级医生一起去手术,手术后大家一起吃顿夜宵,既传授了手术技巧,又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所以科内的同事常说:徐主任群众关系很好。
在凤凰古城和中山眼科、同仁眼科从事眼整形的教授合影(宋维贤,范先群,李冬梅等)
虽然大部分是眼部整形手术,但也有白内障、视网膜脱离等眼科常规手术。那时国外已兴起人工晶状体植入术,但国内尚无进口人工晶状体,我科还自制人工晶状体(虹膜囊膜固定型)用于临床,也曾在《中华眼科杂志》报道。在视网膜脱离方面,我看到国外Lincoff发表了一篇“不放视网膜下液的视网膜脱离手术”一文,我也将积累的数十例类似临床资料撰写成文,刊登在《中华眼科杂志》,这是国内发表的有关视网膜脱离的第一篇文章。
随着追求美的人越来越多,医疗美容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遍地开花,良莠不齐,手术后造成的并发症也越来越多。另外车祸造成的眼面部和眼眶的损伤也显著上升,因此以眼睑组织修复为主的眼整形和眼眶外科已成为眼科学的重要分支。我相继出版了3本眼整形专著:《眼整形手术技术》、《实用眼整形美容手术》、《眼整形美容手术》。并受邀参加Bosniak主编的《PrincipleandplasticOphthalmicPlasticandReconstructiveSurgery》编写工作,参加该书编写的有位全球眼科整形专家,并于年以第一和第二卷形式出版发行。另一国内受邀参加编写的是医院赵光喜教授,遗憾的是他已于数年前仙逝,但他对中国眼整形事业的奉献精神永远激励年青一代奋进!
年,Perry用羟基磷灰石(HA)作为眶内植入物应用于临床,我国于年将HA引入中国市场,随后医院联合上海民政工业研究所朱荣法工程师,在上海及华东地区进行HA推广,逐步改善了眼球摘除术后致残患者的外观,也先后对HA眼座的植入方法及眼座暴露的处理等问题进行了改进和创新。我也主持并参与了北京创意生物工程新材料有限公司举办的多期羟基磷灰石临床应用研讨会,对扩大羟基磷灰石在眼座和骨片的应用和减少并发症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有鉴于此,我荣幸地被聘为创意公司的终身高级顾问。
在从医的生涯中,有几件事至今感到遗憾,难以释怀。大约在20年前,我应医院(现为江医院)手术,有一4岁男童,是南昌市卫生学校校长的儿子(医院外科主任),患单眼先天性上睑下垂及多器官畸形。在第一次到南昌手术时,该院麻醉科副主任会诊后,认为全身麻醉风险较大,拒绝为其全身麻,故放弃手术。次年,我又去该院,患儿父亲再次要求为其子手术治疗,但麻醉科副主任依然不同意全身麻醉。其父绕开麻醉科副主任,请麻醉科主任为患儿实施全身麻。在麻醉过程中,使用一种叫做“加压器”的仪器,当我成功完成手术,进入休息室后不久,传来了患儿在紧急抢救的消息,并根据病情,邀请全南昌市的麻醉科医师进行大会诊,终因患儿广泛肺泡破裂、皮下气肿而宣布不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自此以后,在他院手术时,对全麻的安全性是我首先重点考虑的因素。
还有一件事,是一位早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已退休的外科主任,医院老院长郭秉宽教授的同班同学,一只眼因“青光眼”已失明;另一只眼仅存0.3的视力,管状视野、虹膜广泛后粘连、晶状体混浊。本来医院就诊,因为眼压难以控制在正常水平,医院眼科主任推荐我为其手术,那时我年轻,胆子也大,就接受了邀约,收住我科治疗。术前,医院郭秉宽教授、副院长殷汝桂教授、王文吉教授前来探视,那时,这位患眼疾的外科主任已是75岁高龄,我拟给他做“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手术时发生了从医以来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当做好巩膜瓣即进入前房时,虹膜、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逐一溢出,发生了“脉络膜驱逐性出血”,直至眼内容物全部溢出才逐渐停止,最后的结果是术眼失明、眼球萎缩。因为患者是单眼残存视力,术后双眼失明,我感到非常内疚,一年后,我骑车路过复兴中路时,看到这位患者手持拐杖,在老伴的搀扶下,迎着落日余晖,蹒跚在人行道上,我深深地感叹:一个人如能拥有一双明亮的双眸该有多么重要,也深深领悟到我们所从事的眼科学专业具有重要的责任和崇高的使命。
还有一位年轻患者,曾出现间歇性复视,检查时并未见到眼肌运动障碍,我建议到神经科会诊检查,过了几个月,我询问一位与患者较为熟悉的医生,得知患者已于数周前因颅内出血而去世。还有一类似问题,是在十余年前,有一先天性上睑下垂患儿,于全身麻醉下手术,手术过程顺利,就在出院前一天,患儿要吃甘蔗,其父外出买好甘蔗后回病房,却到处寻不见患儿,最终在厕所的便池旁发现了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的孩子,后经会诊推断,是因患儿脑血管畸形,在大便时屏气,造成脑血管破裂而亡。从这两件事感到,做眼科医生一定要有全局和整体观念。有时眼病的症状可能是另一疾患的表象,也可能同时伴有其他疾病。
时光荏苒,如今我已年过八旬,老树出新芽是不可能了,但老树还未枯萎,只要我手不震颤、头脑不迟钝,我将继续从事我终身为之奋斗的眼整形美容事业。
徐老师的学生们依偎在老师身边,一份缠绵,带一点馨香。
答案及解析请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qky.com/wazlyy/107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