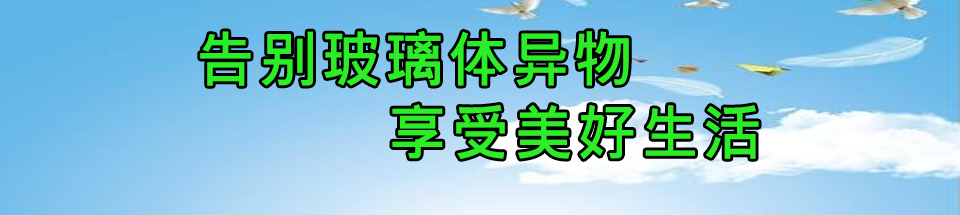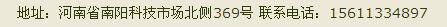每周一品错金豹形器座
错金豹形器座,青铜器,战国文物,器座通高11.2厘米、宽24厘米,銎口长6.5厘米、銎口宽4厘米,年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观音堂村出土。
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
本文由河南博物院志愿者团队采编
原作者:张俊儒
深度
品鉴
从器物造型上看,错金豹形器座整体似一盘卧的豹子。豹子侧身盘卧,头部搭于后腿之上。鼻子隆起,露出两鼻孔;大眼微凸,略向上视;浓眉凸起;近圆形双耳中间内凹。颈部戴扁带形项圈。前左腿支地,足上曲,四爪分明,其中一爪爪牙突出,伸至耳下,似有挠耳之意(图一);前右腿弯曲,四爪并握抱一竖长方体銎管;后左腿股部微凸,足爪不见,隐于銎管及臀下。长长的豹尾弯曲盘于腹背之上。豹体中空,左侧豹身盘卧形成器座底部,底腔有宽约3厘米的内凹折边。豹盘抱的长方体銎管,为两次铸造,銎管上侧口部为第二次铸造形成,有明显范缝痕迹,且微小于一次铸件銎管;銎管下侧,纳于呈“井”字形框架内,二次铸造痕迹十分清晰。“井”字形框架连接于底部内凹的折边上。(图二)
图一错金豹形器座局部
图二错金豹形器座底部的“井”字形框架
从纹饰上看,豹身满饰桔瓣状豹斑花纹。纹饰布局井然有序,头部桔瓣状花纹开口朝前;四肢桔瓣状花纹开口朝向足部;颈部、腹部和尾部桔瓣状花纹以豹子脊椎线为中线,开口分别朝向两侧。每个桔瓣状花纹皆有错金丝勾边,使桔瓣状花纹突显而出。近距离观察,桔瓣状花纹有微凸感,但从豹身部分位置残留的金箔来看,桔瓣状花纹之间的间隙原应嵌有金箔,因大多数已脱落遗失,故使桔瓣状花纹有微凸之感。
该器座造型优美、布局合理、形象生动,具有极强写实感。形态和现在的豹子几乎一致,豹子身体用金箔的黄色表现主体颜色,用嵌金丝的桔瓣状花纹表现豹子的斑点。虽然金箔已大部分脱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但不难想象初成之时的精美。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多有动物装饰,多数是作为纹饰装饰出现,或者以动物形态出现在器物的某一部位,承担一定的功用,如耳部,足部或鋬部等等。这些形态的动物或是缺乏立体感的扁平状,或是夸大动物的某些肢体,写实感都较差,虽也有一些独立形态的动物形器物出现,但是多数也只是表达出动物的造型,像该器既表现动物的形态又能展示动物肤色或皮毛斑纹的写实器物,实属罕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在这件器物上值得注意的是豹子颈部的项圈(图三)。我们知道,人类为了加强对已经降服或驯化的动物的控制,往往在动物身体的某个部位圈套一些装置,如在牛鼻子上穿环、在马嘴上上马衔、在狗脖子上套项圈等等。年在山西浑源发现的牺尊[1],在牛鼻子上就有穿环形态(图四),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重要实物资料”[2]。错金豹形器座豹子颈部套着项圈,可能和牺尊牛鼻子上穿环具有近似的作用,我们无法依此来说明现在属于野生动物的豹子曾经被我们的祖先驯化过,但最起码可以说明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曾经降服过豹子这种猛兽。而且,从该器豹子的姿态、眼睛的形状,也能看出豹子颇有臣服之意。因此,该器对研究我国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图三豹子颈部的项圈
图四山西浑源发现的牺尊牛鼻子上的穿环形态
此外,错金豹形器座竖长方体銎管为两次铸造而成(如图二器物底部“井”字结构部位),第二次铸造使得銎管比一次铸造的部分加高,腔体空间缩小。(图五)从一定意义上说,二次铸造可能是为了达到使纳入銎管内的已经成型的部件更加稳固的目的而不得已的一种做法。但是,这又恰恰显示了我们的祖先在战国时期对一器可以多次浇铸而成的技术的熟练掌握程度。一器多次浇铸成型的技术,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已经开始使用,多用于解决器物的耳部和足部等不易分范的部位与主体部分的衔接问题,后来成为可规模化生产制作青铜器的重要技术手段。而该错金豹形器座仅仅为了使纳入的部件更加合适就再次浇铸以改变銎管的大小,充分说明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比此前的春秋时期更加熟练地掌握了此项技术。因而,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冶金浇铸技术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图五错金豹形器座的俯视图
文化
解读
关于青铜器座,目前国内发现的数量具有一定的规模。之所以称其为器座,主要是因为不能准确界定完整器物实际用途,而保留的青铜器物部分具有明显的器座的一些特征,因而以此命名。当然,已经明确了其用途的,多以其用途属性命名,如帐架座、钟架座等。该类器物主要出土于大型墓葬之中,很少一部分出现在中小型墓内,窖藏中几乎不见。从时间上来看,商代和西周时期几乎没有发现;从春秋开始直至东汉,相对发现较多;东汉以后较少。
年,河南省光山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合葬墓[3]中出土的一件黄夫人方座,高13.6厘米、底边长15.2厘米、底边宽14.7厘米。器呈盝顶形,上部有一方形插座,直通器内底,插座中间位置有两穿孔;下部为方体结构,中空。(图六)
图六河南光山出土的黄夫人方座
年,安徽省屯溪市弈棋飞机场春秋墓葬M3中出土的一件夔纹铜方足器[4],高14厘米、底边长11厘米。器上部为圆柱形銎,下端有圆箍,箍下有穿孔;器下部为器座,弧壁方形结构,内中空。(图七)
图七安徽省屯溪市出土的夔纹铜方足器
年,淅川和尚岭春秋晚期楚墓[5]发掘出土的一件龙纹器座,通高22厘米、底座边长19厘米。器座呈正方形台状,上部四面收成弧形,中间有一八棱长管,管上有四圆穿,管下有方台与器座相连。(图八)
图八淅川和尚岭出土的龙纹器座
年,浙江绍兴狮子山战国前期墓葬[6]出土的一件人形足器座,高15.6厘米、边长16厘米,重10千克。器座由承插柱、座体和四人形足三部分组成,上部承插柱上端为中空的四面八角体,下端弧扩成四面体,四面各饰螭首相背的蟠螭两条,缠绕的螭体间留出两钉孔;座体为方形盝顶结构,内中空,下边有四人形足。(图九)
图九浙江绍兴狮子山出土的人形足器座
年,河北平山县发掘的战国时期中山王墓[7]M1出土的三件错金银器插座。其中错金银虎噬鹿插座,高22.9厘米、长51厘米(图十);错金银犀形插座,高22厘米、长55.5厘米(图十一);错金银牛形插座,高22厘米、长53厘米(图十二)。三件插座造型分别为四足着地的虎、犀牛和牛,兽背皆有长方形銎。
图十河北平山县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插座
图十一错金银犀形插座
图十二错金银牛形插座
年,河北满城汉墓一号墓出土的五件虎形器座(图十三)和两件圆盘形器座。五件虎形器座,大小相同,高5.1厘米、长7.9厘米。“作卧虎形。虎昂首翘尾,颈束宽带装饰,背部作凹槽以嵌插木器,凹槽前后两侧作长方形板状饰,使凹槽加深,有长冒钉从虎项下穿孔通过虎身、凹槽,只贯尾下。当为固定所附木器而设。鎏金。”[8]另有大小相同的圆盘形器座两件,高2.4厘米、径7.4厘米,上部作束颈小口以插置木器,内中尚有朽木残留。器表鎏金。
图十三河北满城汉墓一号墓中出土的虎形器座
年,江苏省苏州市盱眙县大云山汉墓出土了4件兽形器座[9],形制、大小相同。整体呈立兽装,四足着地,背部正中有一方形銎口。
从各个时期的器座资料来看,主要集中在春秋至两汉时期。无论哪个时期的器座,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带有可以纳入其他构件的銎管或插孔。这也是定性其为器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多数器座在出土时还残留有木质构件残段,故而推断该类器座多是上部为木质构件的一类器物的下部器座部分,起到支撑、固定上部构件的作用。因为器座承托的上部木质构件功用性能的不同,木质构件的粗细需求也会有所变化,从而导致銎口的大小也各不相同。战国早期以前的器座,多为单件,銎口变化较多,有方形、长方形、八角形、圆形等,但銎径皆较小。故而推测,此时期的器座承托的上部木质构件多为较简单、轻便的类型(类似于年山东长清县仙人台邿国墓出土鸟饰支架)。动物形态器座偶有发现,但造型多为抽象形态,写实性较差。如淅川徐家岭九号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两件神兽,其中一只神兽臀部一侧就有方形銎口;战国早期以后的器座,銎口形状不再呈现此前的多样性,而多为长方形,偶有正方形,可能此时的器座上部木构件部分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劈料模式即木构件作成截面为长方形的作法。此外,除銎口的变化外,器座的座体部分也有变化。战国早期以前的器座,座体部分多为空心结构,几何状较多,抽象动物状偶有发现;战国早期以后的器座,座体部分多为实心结构,写实动物状较多、几何状几乎不见。
河南博物院藏错金豹形器座,从造型结构上来看,类似于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的虎、牛等器座,皆为写实性动物形态,动物也为常见动物。但是错金豹形器座豹体中空的构造特点又和战国早期及其以前的器座中空构造一致。因而,笔者认为错金豹形器座应是晚于春秋晚期淅川徐家岭九号墓出土神兽和战国早期浙江绍兴狮子山人形足器座而又早于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虎、牛等器座之间的器物。由于青铜豹形器座銎口较战国早期及其以前的各种器座的銎口要大,故而,笔者推测青铜豹形器座的功用可能与战国早期及其以前的器座的功用有所区别,而近似于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器座的功用,如屏风座。
器物功用性质是器物定名的关键,但是一些器物的实际功用往往较为模糊,由于这种模糊性导致不同个人对同一器物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就会产生同一器物不同命名的现象。笔者在本文中所命名的错金豹形器座,只是笔者个人对这一器物功用不同见解而已。至于该器是否具有曾经命名的错金银豹镇的镇的功用,笔者将在下文中作进一步探讨。
比较
研究
年发现于河南陕县观音堂村的豹形器[10],由当地村民发现,后捐献与当地文物部门。因不是正式考古发掘材料,故而极少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介绍和研究。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该器为战国时期的席镇。笔者对豹形器的功用有一些不同的理解,虽在“文化解读”部分列举了一些器座的材料加以佐证,认为豹形器是器物残存的器座部分,但并不一定就准确、全面。因而,笔者在此再列举一些有关镇的材料与豹形器进行对比,对其是否具有镇的功用作进一步地探讨,从而达到对豹形器更加全面、客观的了解的目的。
关于镇,已知最早的,是出土于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西周墓中,但只为孤例;春秋时期有少量镇出土,式样已初步定型,如浙江绍兴印山春秋墓出土的玉质秤砣状镇;战国时期出土的镇较多,有秤砣状、器盖状和动物状等;两汉时期,镇的数量达到巅峰,造型多以虎、豹、凤鸟、辟邪、羊、鹿、熊、龟和蛇等动物为主,装饰手法包含有鎏金、错金银和嵌贝等,除部分人物造型的镇外,几何形态的镇极少出现。
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墓中发现一件兽面形镇(图十三),“青铜铸成,内包两圆石,外铸兽面,器形呈椭圆形。径10×8、高3.8厘米。”[11]
图十四陕西宝鸡出土的兽面形镇
图十五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蟠龙席镇
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两件蟠龙席镇(图十五),通高8厘米,直径11.8厘米。“形如器盖,半球形,内空,平口沿。顶有衔环龙形钮,面部铸八条相互纠缠的龙,空隙处分布十四个凸起的小圆圈。此器同出四件,当为压席之物。”[12]此外还有如器盖状的金镇(图十六)出土,造型与湖北九连墩楚墓出土的青铜镇[13]相似(图十七)。
图十六湖北随州出土的器盖状的金镇
图十七湖北九连墩出土的青铜镇
年,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的战国晚期大府卧牛(图十八),高5厘米、长10厘米,牛作俯卧状,牛首回顾,前膝双跪,后腿屈于腹下。通体饰错银云纹。腹下有铭文“大府之器”。[14]
图十八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的大府卧牛
年,山东平阴孝直镇出土的战国晚期嵌松石卧牛(图十九),高9.7厘米,长14.5厘米。“牛呈卧姿,犄角两分,双耳横直,腿蜷曲,一蹄外翻。尾盘曲臀部,作回首顾盼状。通体镶嵌绿松石。”[15]
图十九山东平阴孝直镇出土的战国晚期嵌松石卧牛
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四件错金银镶嵌豹形镇(图二十),形体大小相同,高3.5厘米、长5.9厘米。“错金银镶嵌,造型优美,栩栩如生。豹作蜷卧状,昂首张口,长尾从腹部向脊背弯卷,平底……豹体内灌铅,使其更加稳重。这类器物可能是作为书镇之用。”[16]
图二十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四件错金银镶嵌豹形镇
年,山西朔县出土的西汉晚期的龟形镇(图二十一),高6.3厘米、长13.9厘米。“卧龟形,龟首扬起,两侧刻有鳞甲,爪微露,平底。腹内中空,背嵌虎斑贝。”[17]
图二十一山西朔县出土的西汉晚期的龟形镇
年,安徽合肥建华窑厂工地出土东汉鎏金熊镇(图二十二),高5.1厘米、宽4厘米。“熊呈蹲坐状。首向前探,张口直视,双耳并立,前肢自然抬起,后肢弯曲,下有一短尾。器表受土侵蚀鎏金部分脱落。造型生动,憨态可掬,多为镇席之用。”[18]
图二十二安徽合肥建华窑厂工地出土东汉鎏金熊镇
汉镇成套的除上述列举的一些外,考古出土的还有很多,如江苏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出土的四件鎏金铜虎[19]、广西台浦西汉木椁墓出土的四件山兽镇[20]、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的三件错金银铜虎[21]以及近年刚发现的江苏大云山汉墓出土的四件鎏金嵌宝石豹镇[22]等。
从西周至两汉时期出土的镇的资料来看,西周个别墓葬中开始出现镇形器物;春秋时期偶有发现,造型接近后代的镇;战国时期发现较多,采集而来的多为单件,墓葬出土的多成对出现;到两汉时,镇大量出现于墓葬之中,且多为4件一套,也有6件一套(上世纪80年代在江苏盱眙县南窑庄穆店窖藏中出土一件汉代黄金伏兽,头上有提环,兽身刻“黄”、“六”二字,故根据铭文推测可能为六件一套)。
无论哪个时期的镇,都明显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器物底部皆为平底,重心多在下部;二、器物上部皆无銎管部件,部分镇上部带有方便提拿的提环;三、镇体多为实心结构,极少部分镇为空心结构,而且一些空心镇,为了增加重量,还要在腔体内灌注铅、石等材料;四、镇的尺寸一般都较小,长度超过15厘米的极少。
从镇的结构特点与器座形器比较来看,两者因为都有下部稳固的功能需求,底部都呈较为相似的平坦状或多支点状,因而底部的结构特征不能作为区别器座形器和镇的依据。那么河南博物院藏错金豹形器是器座还是镇,还要从其它部位着手:错金豹形器内部为空腔,且有固定銎管的井架结构,虽然有一些镇的体腔为中空构造,但都没有与豹形器井架结构类似的部件;错金豹形器尺寸过大,最大径可达24厘米,相当于大多数镇尺寸的二倍或三倍;错金豹形器上部有銎管,可供插置木质构件,而镇皆无此部件,部分镇的上部带有的提环也与銎管的功用差距较大。从错金豹形器内部结构和尺寸大小上来看,虽然与镇的结构和尺寸有不同之处,但是要作为区别器座形器和镇的依据也有些勉强。如此看来,有无銎管才是区别错金豹形器是器座还是镇的关键。但将错金豹形器看作是席镇的观点认为,豹形器作压席的镇,放置于席的四角,銎管可以用来插入帐架。这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銎管存在的原因,但仅凭一件孤例,就将错金豹形器看作是镇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目前有关镇的研究的文章或学术报告也从未例举有带有銎管的镇的例子。而此观点的立足点是将器座和镇的功用合二为一即青铜豹形器同时具有镇和帐架座的功用。从发掘的墓葬资料来看,镇和器座形器经常同出,作为生活类随葬品,代表某一类功用的器物随葬一件或者一组足够,那么同出的镇和器座形器显然是分别代表不同功用的两种器物随死者随葬的。因而,笔者认为,将错金豹形器看作拥有两重功用的镇及帐架没有充分的依据,銎管的有无才是判断青铜豹形器功用的关键,即错金豹形器只是通过銎管来承托上部木质构件的一个器座,至于是否同时具有镇的功用,还有待更多类似考古材料的出土来加以佐证。
趣味
猜想
猜想一:错金豹形器座銎管为竖长方体结构,銎径也比一般的器座銎径要大,那么插入銎管内的木质构件是做什么用呢?是复杂的木作结构,还是简单的木作结构?
猜想二:错金豹形器座作为承托木质构件的器座部分,制作成带有项圈的盘卧状豹子而不是其他动物,是为了和上部的木质构件相协调,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相关
链接
青铜器上的错金银工艺
错金银工艺现在一般是指应用于青铜器上的一种装饰工艺,也可以说是对青铜器器表进行装饰美化的一种技术手段。从考古资料来看,错金银工艺出现在春秋中晚期的青铜器物之上,多数在兵器之上;到战国时,这种工艺已较为成熟,除了兵器之外,还应用于车马器和较大的容器之上;两汉时期,错金银工艺十分成熟,使用这种工艺的器物几乎可以涵盖各个门类,小到一个部件,大到完整器体。现在发现的实物资料也主要集中在战国至两汉时期。
青铜器上的错金、错银或错金银工艺,古代称为金错、银错或金银错。关于错金、错银的文献记载比较多:如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记载的“金错蜀杯”;《汉书?食货志》记载的“错刀以黄金错其文”;西汉张衡《四愁诗》记载的“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司马彪《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的“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诸侯王黄金错”;曹操《上杂物疏》记载的“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皇太子杂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等。说明错金银工艺在两汉及其以后曾被广泛的使用,人们对该工艺也十分熟悉。
错金银工艺从字面理解,是用“错”的方法或手段将金或银装饰到某种器物之上的一种工艺。金、银指的是装饰所用的材料,“错”指的是装饰时使用的方法。所以,对错金银工艺的理解关键在于对“错”的理解。各种辞书对“错”的解释至少有十多种,但与金属相联系的解释都较为近似。许慎《说文解字》:“错,金涂也,从金昔声。”清段玉裁注释:“涂,俗作塗,又或作搽,谓以金错其上也。”《辞海》:“错,用金涂饰。”由此来看,错金银工艺就是将金银材料图画于器物之上的一种手段,将金银涂画于金属器上和涂画于其他材质器物上的工艺都可以称作错金银。如《西京杂记》卷一记载有“金错绣裆”,是用金钱绣成图案花纹的背心。《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的“金漆错”,是在漆器上作出金银图形。
错金银工艺的装饰题材和内容,主要可分为铭文、几何形图案和生物形态等三种类型。
一、铭文。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常铸、刻有铭文,但多在器物的内部。错金银工艺发明后,为了增加器物的美观度或突出铭文的重要性,将刻铭与错金银工艺结合,使铭文的位置从原来的器内、底部等不显眼部位转移到器物外部明显部位。错金银的铭文也多采用十分美观的鸟篆书。春秋至战国早期,错金银铭文多用于兵器上;秦汉时期,则多见于鼎、壶等容器之上。
二、几何纹图案。最长用的是几何云纹,采用细而匀称的云纹涡线勾勒主体框架,云纹涡线之间用较宽的面来联结。此外,还有菱纹、三角纹、雷纹、勾连纹等。几何图案的运用,是战国至秦汉时期错金银工艺的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这类图案多见于车马器和一些器物的部件之上,部分容器也有使用。
三、生物形态。这类题材主要有动物纹、狩猎纹、人物纹、植物枝蔓花瓣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青铜器的眼、眉、鼻、嘴、爪、毛和羽等器官的形态等。战国晚期开始较多使用,多装饰于较大的容器之上。
错金银工艺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镶嵌法和涂画法两种。用镶嵌法制作的器物,我们现在还称之为错金银器;用涂画法制作的器物我们现在则有错金银器和鎏金器两种叫法。区别涂画法制作的器物是错金银器还是鎏金器,关键是看涂画于器表的金银是否用线条勾勒轮廓。用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的,仍叫作错金银器,而通体素面,不用线条勾勒轮廓的则称为鎏金器。
镶嵌法。在史树青先生的《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认为该工艺制作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作母范预刻凹槽,以便器铸成后,在凹槽内嵌金银。第二步是錾槽。“铜器铸成后,凹槽还需要加工錾凿,精细的纹饰,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錾刻浅槽,这在古代叫刻镂,也叫镂金”。第三步是镶嵌。第四步是磨错。“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必须用错(厝)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
涂画法。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的实物,其制作工序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将金银放入坩锅内加温至摄氏四百度以上,然后再加入为黄金七倍的汞,使其溶解成液体,制成所谓的“泥金”即“金汞剂”;第二步,用“泥金”在青铜器上涂饰各种错综复杂的图案纹饰,或者涂在预铸的凹槽之内;第三步,用无烟炭火温烤,使汞蒸发,黄金图案纹饰就固定于青铜器表面。
注释:
注释:
[1]商承祚.浑源彝器图[M].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马今洪.牺尊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李峪村青铜器[J].上海文博论丛,(2).
[3]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J].考古,(4).
[4]安徽省博物馆编.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淅川县和尚岭春秋楚墓的发掘[J].华夏考古,(3).
[6]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绍兴地区文化局,绍兴市文管会.绍兴号战国墓发掘简报[J].文物,(1).
[7]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
[8][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
[9][22]因系统性的考古发掘报告至今还未正式出版,只从一些媒体和网络中获取较少的信息。依据图片和描述,笔者做出的判断可能会有误差,具体信息以将来出版后的正式报告为准。
[10]笔者在此前曾用“青铜豹形器座”命名,并列举一些器座加以佐证。但在此章节,笔者试图以镇的角度对该器是否具有镇的功用进行比较研究,若用“青铜豹形器座”这一名称有失妥当,故而暂以“豹形器”说之。
[11]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4).
[12][14]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0[M].北京:文物出版社,.
[13]湖北省博物馆.九连墩——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大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
[15]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9[M].北京:文物出版社,.
[17][18]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2[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J].文物,(4).
[2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台浦西汉木椁墓[J].考古,(5).
[2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
作者:张俊儒
张俊儒,男,吉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学士,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馆员,主要从事夏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与鉴定。
hbvolunteer
河南博物院志愿者团队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qky.com/wazlyy/6063.html